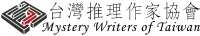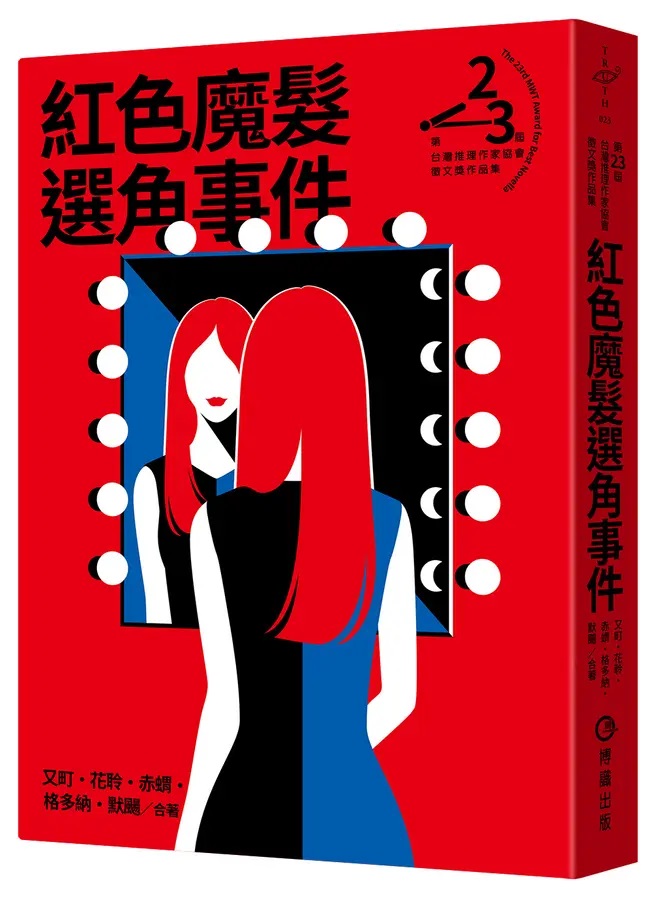本屆決選評審共五位,分別為(依筆劃順序排列):
杜鵑窩人、唐福睿、張亦絢、路那、陳蕙慧
本屆五篇決選入圍作為(依來稿順序排列):
〈大盜唐飛龍〉、〈二婆洗冤:安平王城案〉、〈狼人誕生之處〉、〈紅色魔髮選角事件〉、〈破地獄〉
以下為各篇之決選會議紀錄。
〈大盜唐飛龍〉
張亦絢:
我覺得作者應該對漫畫館的成立有很深刻的理解,這部分的細節寫得滿生動,也可以看出作者有一定的考據。但在寫作技巧與敘事轉折上,仍略顯薄弱。
這部作品借用推理的形式,主要來傳達其他主題,我稱這樣的作品為「偽推(理)」作品,即它借用了推理小說的外殼,但其真正關注的,其實是別的主題。這樣的創作形式在校園文學場域中常見,只是得更清楚地意識到:既然選擇了這個形式,就要知道「偽」該如何安排——例如漫畫與推理兩者的比例、融合方式。
其實漫畫與推理本來就有某種共振性,它們一開始都並非主流或精英文化,是可以相互參照的,但像把漫畫館移址寫進去這件事,我就會覺得不是特別有必要,甚至流於個人抒發。小說裡傳達了一種「真正愛好者」的對抗態度、對物件持有的執念,這樣的意念雖然有傳達到,但稍微缺乏說服力,但它有與推理愛好一事對話的潛力,是本作有力的部分。小說應該假設讀者可能是完全反對你,甚至一無所知的,若能從這樣的角度出發,說服力會更強。
路那:
我同意亦絢老師的意見。讀這篇時我一開始也想說「該不會作者本人就是參與過相關事務的人吧?」因為裡面提到很多細節,非常熟悉。我第一遍讀完覺得是個好看的小說,但有哪裡怪怪的,卻說不出來。等我重新回頭思考,才發現:「欸?這篇有推理嗎?」
這篇作品有一個很輕的謎團,確實沒有實際的「盜竊」,而是從另一個層面去解構「偷」這個概念。它不是在講一個具體的犯罪事件,而是透過漫畫的敘事,以及小說的後設,來處理對「犯罪動機」的詮釋。因此在閱讀這小說時,會在第一次閱讀以及第二次讀的感覺,會有很大不同的反應。特別從「反推理」的角度來說,這篇小說並不是在追求犯罪行為,而是更關注背後的動機,動機又再一次解構行為.這反而讓它顯得頗有意思。這類型「另作解法」的類型,如果讀者先一步推敲到結局,效果會大打折扣,但這篇也沒有這樣的問題。
我還滿欣賞它屬於「日常推理」這一點,沒那麼沉重,也不打打殺殺,是可以真實發生的事情。而這個「日常性」其實也支撐了它在官僚與愛好者的對抗這條主線——它有意識地用多重角度,讓讀者去看待制度與個體的衝突。
不過,我也感覺作者其實也避免只有存於愛好者的視角,儘量客觀描繪官僚體制的現狀與困難,同時官僚主義也確實存在,層次很分明;以及精準描繪愛好者的掙扎,這部分也很清楚。只是我還是會有一點點擔心,這樣的閱讀是否也是我的一種過度詮釋?
唐福睿:
這篇其實是我五篇中給分最低的一篇。我最喜歡的地方,也如路那老師剛提到的,是它的「日常」。這種看似日常的事件,其實我們每天都可能碰上,
因為我們預設推理小說會有很極端的情境和人性衝突,但用推理小說來處理這類衝突,對我來說是滿有趣。
然而讀完以後,我回頭檢視推理元素,就會覺得好像缺了一點什麼。
當然我理解作者想用推理的形式,包裝一個對「官僚與倡議者」衝突的觀察,像是官僚與愛好者之間的矛盾與彼此的難處,雖然作者描寫得很仔細,但整體來說,對我而言這些描寫都太可預測,沒有讓我感覺到新意。
如果推理只是包裝,那麼接下來就會更在意人物是否夠吸引我,是否有趣,就算處理的主題和衝突可以想見,只要人物有趣,我還是會很在意人物最後能否得到他所要的;可惜這篇裡的人物也沒讓我產生太多共鳴。雖然不是不有趣,但就是有種「平淡」感。也許因為我過去受到劇本訓練,我會特別看重「強概念」或者「有趣人物」,這兩者能才讓我在閱讀中獲得娛樂性,但這篇在娛樂性上是比較可惜的。
杜鵑窩人:
這種「日常推理」的類型,我習慣區分為「解謎」與「推理」。這篇作品在小說層面是沒問題的,但推理部分就比較弱。
尤其關於「偷」,一般社會通念都認為是拿走,這部裡面是放進去,到底是增加?還是減少?這種從「偷」的定義來探討「破壞」,這個概念很有意思。日常推理的有趣之處,便是解構這樣約定俗成的習慣。
至於官僚的描寫,我覺得寫得很真實,可能是作者自己也受過傷,或者觀察很入微。但總體來說,這篇小說完整、敘事清楚,但推理與合理性比較可惜。
陳蕙慧:
我會用六個字來歸納這篇作品:處處對號入座。意思是說,作者的概念和結構其實很清晰,也試圖用一個具吸引力的主題來吸引讀者,把所有要素盡可能塞進去。但我覺得他用力過猛,導致整體太擁擠。從小說技藝的角度來看,這篇是不夠成熟的。
他想把所有東西都放進來,包括人物設定、情節安排、敘事語調與謎團設定和解決,但反而失去小說該有的節奏與層次感,變成只是在「說故事」。對我來說,雖然可以欣賞到他的用心與熱情,但閱讀的樂趣就沒有了。
這其實很可惜,這個作者其實很有機會,他有宏觀的視野以及企圖心,包含對於竊盜的解構,但是這篇過多的篇幅在抱怨,實在很可惜。
小說不是寫議題報告,語言的溫度與層次很重要。但這篇讓我覺得像是在看行銷提案、官方報告,過於口號化、扁平化,也缺乏對讀者的想像與引導。
我會建議他回頭去看《八尺門的辯護人》和《永別書》,看看怎麼樣透過角色行動、細節展現,讓意圖內化進敘事結構裡,而不是只靠台詞與宣言來表達。
張亦絢:
我也會建議小說中的地名、機關可以用「中部最大的城市」,不要直接使用「國家漫畫館」這些實名,會讓讀者分不清這是小說,還是要爆誰的料,其實會干擾小說。
〈二婆洗冤:安平王城案〉
路那:
我對這篇的感情其實很複雜。一方面我覺得它是很難得一見的歷史推理,尤其是臺灣本地的作品,這樣的題材與寫法真的很稀有,我非常認同作者下了很多考證的工夫,可是一方面,我真的「喜歡不起來」。
我自己最大的困難點在於那種很《臺灣奇案》式的風格,還有大量的唸白、台語語氣,我讀起來是有點跳的。再加上整體的反轉太多,層層堆疊之後顯得有些粗糙,我會覺得作者好像很急著把情節往前推,反而讓人物的行動邏輯變得不那麼可信。
像是沈藥婆的動機雖然是復仇,但她做事的方式有時候讓我有點不懂她到底是怎麼想的,抱持報復的心態陪著鄭穩婆查案,包含她的心理轉折,還有對搭檔的信任,也都讓我覺得有點「理所應當」。這篇的優點在於巧妙融合歷史和推理.但謎團的推理邏輯推演並不能說服我,讓我走進這個故事。
當然閱讀歷史推理要容忍一定程度的錯誤與虛構,但是還是有一些我覺得有疑慮的部分,像明朝應該沒有御史中丞這個職稱:由於鄭成功改名「東都」,「大員」或非是鄭穩婆會使用的指稱等。
唐福睿:
我其實滿喜歡這篇的。剛剛路那老師提到那些歷史考證的問題,並沒有影響到我,因為我不是研究歷史的人,我會很自然地接受作者所創造的世界觀,覺得那些官職、稱謂就「好像真的有這樣的事」,這對我來說反而是某種說服力。
我很喜歡這部作品的「概念」以及「人物」,尤其是兩位女性角色共同辦案,這在那個時代背景下非常具有張力。女性甚至不能直接與將軍對話,但她們卻得一起去面對敵意與階級的壓力,完成破案,這對我很有吸引力。在人物設定上,尤其是其中那位仵作的角色,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在那個時代的官場裡,會有女性來扮演這麼關鍵的位置,基本上我沒有大多障礙進入這個故事。
當然,它在某些解謎的地方確實比較鬆,有時候主角的知識太強大了,和讀者不對等,尤其在藥理和《洗冤集錄》的部分,變成她說什麼都算,就少了讀者一起解謎的參與感。
不過整體來說,我覺得這篇的娛樂性很強,而且真的提供了我沒看過的內容,營造出一個混亂又動盪的臺灣時代感,讓一個小案件牽動整個政權結構和時代走向,這真的太吸引我了,所以我給了很高的評分。
杜鵑窩人:
我也是滿喜歡這篇的,沈藥婆也是一個黑化的華生,尤其是它的娛樂性非常高。
裡面很多細節你要說是不是正確的,我覺得可以不用太嚴格去要求,就像我自己很喜歡《黑牢城》,雖然裡面的對話根本不是那個時代的人會講的話,但我還是很享受。
路那:
我要澄清一下,我講的並不是《黑牢城》這樣的狀況,如果是《黑牢城》那處理的會是誰來即位的問題,而不是歷史用語的與史實不符。
杜鵑窩人:
另外我也覺得這篇的說故事能力真的很好,沈藥婆一直不斷誤導,主角也設法一一破解,但問題也是如唐福睿老師所說,給予讀者的挑戰不夠。不過這篇陷阱設計得也不錯,而且它的篇幅控制也滿好的,有把該說的說完,所以我這邊給它的分數是滿不錯的。
陳蕙慧:
這篇在結構上是非常完整的,翻轉的意外性都處理得不錯。我特別喜歡人物之間的互動,對話的節奏也很好,情緒鋪陳也不錯,這些都看得出來是有寫作功力的。
不過要論題材的新意上,我認為這篇稍嫌不足,他的創新在於「現代性」的進入。我一直認為歷史推理裡最重要的,是要讓現代的讀者感覺到「這個問題跟我有關」,也就是要有「現代性」。我看到的是兩位弱勢的女性的失語,如何在一個壓迫她們的時代中互相幫助、互相信任,這個部份我很喜歡,以及作者沒有明講,但讀者可以感覺到她們之間的那種情感與曖昧。
我有一點點在意的是它的語言風格,它用了半文言半白話的方式來處理,有一點像說書,這會稍微減弱它的現代性,這讓我有點遲疑。但總體來說,我覺得作者有很強的說故事能力。
張亦絢:
這是我最喜愛,也最多批評的一篇。
我先說結論好了,我想我會反對這一篇。要用一個比喻的話,這就像是一道菜端上來,擺盤很漂亮,醬汁也很棒,結果菜是生的。我覺得它是一個「富麗堂皇但沒有地基」的作品,因為缺乏人物情感以及敘事的核心,失去了地基。
我有多喜歡它的貢獻,以女性的角度,對於臺灣史和性別史的處理,我就越要更嚴肅看待。
我要呼應一下蕙慧提到的現代性,現代性有一個危險的問題,我們是否用現代的觀點和需求,投射到古代。我也可以接受在歷史細節上的錯誤,但我真正在意的是「史感」,我不求有到史家的深度,但至少要達到中等的水準,我所在意的是它的轉折太多,導致前後互相抵消,像是復仇的情感線,這個力量是被削減的,最後並沒有好好處理收尾,故事的情感到最後沒有真正爆發。
我覺得,推理小說的現代性不在語言或用字,而是在整體的觀念與結構上,如果這篇小說得獎,我也覺得確實會引發某種震撼,但問題是,如果再有一個參賽者採取臺灣議題和性別關環的相類書寫,但是敘事上同樣存在某些缺陷,應該就很難得到同等的寬容。我認為如果不能傳達對敘事整體性的重視程度,可能對作者們會造成混淆的影響。
陳蕙慧:
先不論是否評選這篇作品為第一。有的時候反而正義伸張的懸而未決是呈現那個時代,好讓我們觀照現今。我覺得謎團有解決,翻轉具有意外性,我就可以接受了。
〈狼人誕生之處〉
唐福睿:
《狼人誕生之處》對我來說是一篇「持平」的作品。閱讀過程我其實是被娛樂到的,它創造了一個奇幻世界,而且很容易理解。角色和職業的設定都很清楚,讀者一進去大概就能理解這個世界會怎麼運作。
我自己很熟悉這類題材,我喜歡打電動,也愛看奇幻作品,所以我蠻能投入的。故事融合了「師徒關係」這個蠻有趣的元素,主角是個年輕人,透過他的視角探索案件,有陷阱、有誤導、也有轉折。尤其當他發現自己的師父竟然才是真正被遺棄的那個人,這個反轉讓我有驚喜的感覺。
「持平」的原因主要是謎題設計略顯薄弱。像「天仙子」這種迷幻藥的設定,其實前面幾乎沒鋪陳,但最後卻成為解謎的關鍵。我在閱讀時完全沒把它納入線索,反轉揭曉時有點「喔,原來如此」的失落感。
總體來說這是一篇好讀、輕鬆、娛樂性夠的作品。主角雖稱不上有強烈吸引力,但我願意跟著他走下去,查案、追真相。只是,若要評比,謎題的設計相對薄弱。
杜鵑窩人:
我給這篇的分數其實不算低,因為我第一個想到的是前幾屆的得獎者「會拍動」。它的節奏、世界觀、角色安排,都有一種可以繼續寫下去的潛力。我並不期待新手能把細節寫得完美,這是我和既晴以前常吵的點──新手怎麼可能一點疏漏都沒有?那只有天才做得到。
我們這個比賽某種程度上就像新人獎。既然是新人獎,我就不會用成熟作家的標準來看待。這篇小說有故事、有娛樂性、有謎題、有反轉,那我就不會苛求更多。得獎我也不會覺得遺憾。
當然它不是完美的作品,他穩穩的,該有的都有,我給得分數也不低。
陳蕙慧:
這篇小說讓我不滿足的地方在於,它講了一個過於簡單的故事,幾乎是線性敘事,沒有太多挑戰性。在人物描寫上也過於平面了,不夠立體。
他想呈現師徒之情,但表達方式就是不斷搓頭、揉頭,反而顯得單調。還有像那個警備員說「村裡安全都靠你了」這樣的對白,前後邏輯根本對不起來,讓我懷疑作者是不是只是急著把故事寫完,以致最後處理得具有巧思、最有可看性的翻轉失去了後勁,更讓人感到失落。
雖然我認同今年整體水準比往年都好,但若以首獎的標準來看,這篇作品還是太單薄了。
張亦絢:
我其實還沒決定要不要投票給這篇。我承認它在故事整體的照顧上相對完整,也有趣味性。它不是那種過度展現技法或「寫給評審看」的作品,而是比較能夠回歸到閱讀本身的樂趣。
我覺得它雖然簡單,卻在某些主題層次上有深度,比如狼人象徵的「被排除者」的處境。它沒有用太粗暴的方式去處理這一層意涵,反而讓我感覺有餘韻。我對這篇的分數會是相對高的。
我觀察到這次投稿作品有一種現象,為了拿出競賽的搶眼元素或得分項(比如比較重視亮點,但卻未必注意亮點與亮點間配置與取捨,變成有時不惜造成干擾的尷尬),有點失去了寫作本身的自然狀態。而《狼人誕生之處》反而沒陷入這種困境,仍保有一定的「寫給讀者看」的純粹性,這對我來說是加分的。
路那:
這篇給我的印象是四平八穩,該做到的都做到,但也因為太穩了,導致我看不到作者的個性。它像是一個流水線上的產品,而不是一個工藝品。
不過我覺得作者應該對輕小說非常熟悉,用這種敘事節奏寫得非常流暢,角色辨識度也很高。我不會因為小地方出錯就扣太多分,因為整體讀下來是順的、有趣的。
比較可惜的是這一屆競爭激烈,它比較難出頭。
〈紅色魔髮選角事件〉
杜鵑窩人:
這是本次入圍作品中最複雜、最理論性,但也最無聊的一篇,讀起來其實不輕鬆。
這篇讓我最頭痛的是:整篇推理基本上都是「他說、他說、他說」,完全沒有證據支撐。在歷屆評審標準中,這幾乎是「天條」級的禁忌。不論誰當評審,這種推理方式一定會被批評。連冷言老師都曾說過,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這種「沒有證據的推理」與「隔空打牛」。
而這篇就犯了這個大忌。雖然故事本身講得很好、推理也看似紮實,但由於全靠人物說法堆疊出來,沒有實際的邏輯或物證支持,導致最後我的分數直接從最高掉到最低。這樣的形式性錯誤,真的太致命。
另外我還想問:這篇的偵探到底是誰?是導演?編劇?還是演員?故事裡用了「雙雄」,可是真正是誰在推理?如果整篇小說沒有人站出來說「我解開了謎團」,那到底是誰在查案?有沒有證據支撐?
陳蕙慧:
我倒不覺得這篇是最無聊的,第一是我覺得這是這屆入圍中文字能力最好的。在結構上是以劇中劇的方式呈現,案子是虛構劇本裡的事件,試鏡的是一部尚未拍攝的戲,並非現實發生的命案。所以對我來說,導演與編劇就是解謎的關鍵角色。
在書中書、謎中謎裡,是劇本中的小藍和小紅的謎。第二層是演藝圈中的兢爭,因競爭而造成的犯罪。這一段書寫中作者在三個演員的心態揣摩上處理得很飽滿,演員如何詮釋角色、對故事的理解、與導演、編劇之間的關係、爭取角色時的進退拿捏等,這些都處理得立體又真實。而且小說透過對話展現角色性格與情感張力,光是這點就讓我相當肯定。
至於所謂的「敘述性軌計」,我認為也可以套用在導演與編劇的角色上。這是形式上值得挑戰的嘗試,或許不是最成功的結尾,但整體構成仍然讓我樂在其中,連讀三遍都不覺得枯燥。
張亦絢:
我的想法有點綜合兩位,我覺得這篇不是全然「他說、她說」,還是有邏輯推演的部分。雖然最讓我難以接受的是繼承家產那段推理,那個真的太跳躍了,我在讀推理小說的經驗裡,很少見過這麼突兀的轉折。
「拔頭髮」也讓我感到煩惱。推理史中有過著名的描述「頭髮不是那麼好拔的」(按,指«白馬酒店»中的一個細節。感謝杜鵑窩人前輩立刻提供書名)。假設是生前拔髮,那本來就很困難,如果這些情節能處理得更細膩,效果會更好。
不過我同意這篇優點也很多,它是典型「靠說話」來進行推理的劇情。這很有美式推理小說的影子,比如警方辦案過程中如何說話、怎麼聽取證詞、掩飾或不小心說出真相等,這些都靠語言推進,這完全大有可為,也相當好看。尤其是對演藝圈的生態、心理描寫與試鏡壓力等描寫,都有許多可取之處。我覺得他下了很多功夫,這篇對我來說是有大優點和小缺點。
路那:
我看了這篇很多次。這篇結構層次非常複雜,從劇本、紅髮、試鏡帶出偷劇本的真凶。回到偵探的身份,這篇採取讓所有疑犯都會去當偵探,我特別喜歡偵探與犯人角色的翻轉設定:原本以為是偵探的人,其實是一個失敗的犯人,因為破綻洩漏而被識破,這個翻轉很成功,寫作功力也很不錯,層次很多還沒有亂掉。
他也蠻有幽默感的,例如苗族巫師那段,讀到時我真的笑出聲。
不過我有邏輯上的疑問:比如說紅髮是遺傳特徵,那為什麼還染髮的算得進來?這讓組織的辨識標準失去效力。再來是,如果是對警察的障眼法,案情設計裡竟然讓警方無法迅速查明死者的關係與DNA,這在現實操作中太不可信,讓人難以理解怎麼會讓20年前的冤獄因此被重新揭開。
因為作者敘事採取多人討論推導,結構上就沒有辦法一開始全盤揭露,會變成因為漏了,再補上去,如果真相一直疊加,我怎麼會知道這個真相後面有沒有其他真相?
唐福睿:
我其實滿喜歡這篇的。它最吸引我的是,作者有一種明顯的「挑釁」態度,也激發讀者去參與故事、做判斷。全篇是多視角的說法拼接,讓你去思考誰說的才是真的,這種「羅生門式」的敘事方式,我覺得非常刺激。
從一開始,我就不期待這是一個「真實案件」的推理,而是把它視為一個劇本內的虛構劇情。在這個前提下,我覺得許多細節省略反而是合理的,甚至必要的,因為它需要讀者自己動腦。雖然有些轉折會讓人一時錯愕,但整體來說,這個劇中劇的設計非常有趣,他又把編劇、演員,所謂演藝圈的聲帶結合在裡面。
而且我自己是拍戲的人,我能感受到作者對演員與導演工作的理解非常到位。像演員從不同角度切入劇本、思考角色詮釋方式,這些東西非常貼近真實創作現場。這讓我懷疑作者是不是戲劇圈內的人,不然他不可能把這些內部流程與情境寫得這麼真。
結構方面,雖然複雜,但條理分明。角色之間的說話次序、影響彼此判斷的方式、如何反推回來形成新的理解,這些都讓我非常驚艷。雖然邏輯上有些不完美,有些線索略顯跳躍,但這思考的過程很挑戰也很有趣,我也蠻喜歡這一篇。
〈破地獄〉
陳蕙慧:
我認為這篇作品想處理的是「一念之間」的概念,也就是兇案的發生來自一時衝動(至少全篇的敘事讓我把焦點放在了這裡)。但我沒辦法被這樣的設定說服。兇手不僅殺了父親,還打算殺三個人——仇恨真有那麼大嗎?她甚至還要讓父親無法超生。
故事裡不少細節也讓我覺得牽強,比如有人會在岳父的喪禮上噴那麼多古龍水嗎?而且為了講這個大師兄有多可惡,用了一個持喪中吃葷的設定,而顯得他「該死」,這樣的鋪陳太生硬了。另外,夫妻互動也不自然,角色之間湊在一起像是為了劇情服務而生。
我知道他想要傳達的訊息是:人會在關鍵時刻選擇善惡、生死,可是動機處理太單薄。
這部作品對我來說寫得很順,但卻沒有特別吸引我。
張亦絢:
這裡面的「一念之間」,光是靠這一念並不能實行,小說中兇手的詭計並不是兇手自己的想法,而是聽來、借用別人的,這個在日本推理中橫溝正史曾經用過,是相對冷門但很有意思的領域,在這個向度的變奏很有發揮空間,我還蠻高興再次讀到,只不過在處理的細緻度上,還可以再多一點。
情節同時安排了殺外遇丈夫、舊情人、陌生人,甚至還要殺父親,等於是一箭三雕。我對這篇還有個小提醒,描寫時多少要注意不要流於將女性塑造成「萬惡」的形象,因為惡意並不是性別專屬,男女都有可能很惡。在這部分太少反思,會有一點舊派之感。像前任情人對女主角造成的刺激,應該可以再多一點層次,讓讀者感受她的情感和動機,而不是只是單純地以「該死」推進劇情。
民俗元素的部分,我本身並不熟悉,所以有些內容是第一次看到,覺得新鮮、有趣,是很好的嘗試。整體來說故事流暢,但在動機鋪陳與詭計的運用上,我覺得還可以更周延。
路那:
我覺得故事裡的女主角像是一個長期承受高壓的人,有一天遇到觸發點就突然爆發、崩潰。但問題是,作品只讓我們看到她的爆發點,沒讓我們看到那個「觸發點」是什麼;壓力雖大,卻沒有具體鋪陳她壓力的來源,從頭到尾觀眾只看見她爆炸,卻只能憑作者的解釋去理解原因。
再來,我對作品名有意見。這個名字會令人聯想到陳茂賢導演的電影《破·地獄》,雖然「破地獄」本身是民俗稱呼,不能說電影用了小說就不能用,但在現在這個時間點,確實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那部電影。這對作者反而不利,因為如果觀眾看過那部電影,很容易把兩者加以比較。即使用相同的名詞去發展不同的故事是合理的創作方式,但名稱的重疊可能會影響作品被認識的方式,也可能因為電影傳播力太強,讓讀者帶著既定印象去閱讀,結果發現和自己預想的不一樣。
另外,我對詭計的設定有很大質疑,特別是香水的細節。故事設定原本計劃行兇的周克毅預備了200ml的油,這些油完全從瓶子裡消失了,偵探推測是轉移到了另一個瓶子裡。接下來被找出來的瓶子是古龍水瓶,「裡面還大概有半瓶未曾用盡的古龍水」。換言之,這個古龍水瓶的原始容量應該至少大於200ml,才能裝進之前消失的油,還要再加上沒有噴完的原始古龍水容量。但這和現實相差太多——一般人隨身攜帶的香水容量,多是5ml、15ml,不可能一次攜帶到超過200ml。再說,香水的瓶子還多為厚玻璃瓶,不能自行拆裝;若是分裝瓶,也不可能超過15ml。再加上即使是古龍水,氣味也會十分明顯,一般人噴兩三下就能讓周遭聞到,若真「噴了半瓶」,味道一定非常明顯,不可能整間屋子都聞不到。
這些細節在詭計設計上需要更嚴謹的考量。
唐福睿:
我覺得這篇在閱讀過程中,最大問題在於詭計的合理性,尤其是一些細節的過渡處理。像剛剛大家提到的,香水要噴多少、瓶子那麼大等等,確實會讓我出戲。再加上故事裡還特別描寫去尋找那個丟棄的瓶子,但其實丟瓶子這件事並不難,隨便一個窗戶就能拋出去,它不見得會被留在犯罪現場,所以這一點會阻礙我對故事的投入與享受。
這篇對我來說最有趣的地方,是它結合了民俗儀式與親子、家族間的恩怨。我一開始讀的時候,就是期待這種情感層面的衝突。因為我也看過那部香港電影,那部作品給我很大感觸,它的概念是:這個儀式除了超度死人,更重要的是超度活人。所以在閱讀這篇時,我自然會去想,生者之間的恩怨情仇才是核心。
我原本期待能更強烈地感受到這些人之間的情感糾葛,但實際上著墨並不多,特別是執行殺人計畫的這位女性角色,她的心理過程並沒有說服我。這也是我覺得故事可惜的地方。
另外,人物塑造上確實比較刻板,行動和反應都過於可預測。雖然我很喜歡「破地獄」中「生者之間彼此超度」的概念,但故事並沒有真正展現出來。
杜鵑窩人:
我這邊給的分數不高,因為我一次讀完之後,感覺這裡不合理、那裡也不合理,不合理的地方實在太多。像「一念之間」這個設定,一口氣就要殺三個人——外遇丈夫、舊情人、陌生人——這不是正常情況會出現的念頭。你一念之間就能想到要殺三個人,這也太厲害了。
所以老實說,這篇是我看最快的一篇。一口氣就想到要殺三個人,那乾脆直接拿衝鋒槍去掃射算了。
【投票】
杜鵑窩人:〈狼人誕生之處〉
唐福睿:〈紅色魔髮選角事件〉
張亦絢:〈狼人誕生之處〉
路那:〈紅色魔髮選角事件〉
陳蕙慧:〈紅色魔髮選角事件〉
最終投票結果為〈紅色魔髮選角事件〉獲得首獎。